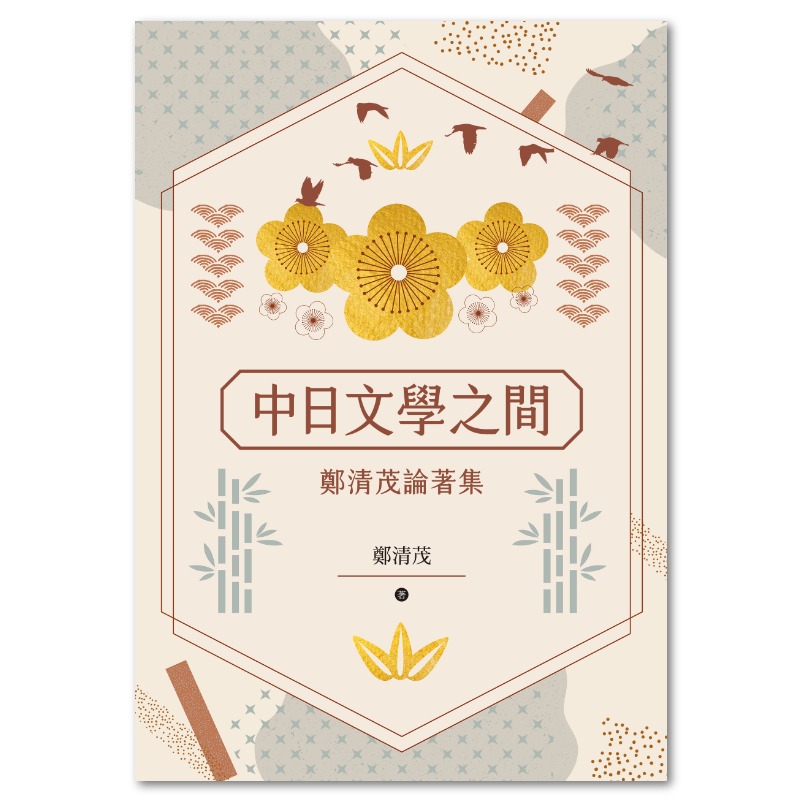桃園作家作品
作品說明
撰筆:張嘉珮
《中國文學在日本》是鄭清茂老師出版於民國五十七年的個人著作。雖然書名如此,但箇中內容卻不僅僅在說明中國文學在日本的傳播過程,而是以流暢且平易近人的文筆闡釋平安時代以降的日本文人如何把從中國文學與哲學思想中受到的啟發應用於創作之上,並且引用了相當數量的作品文章(主要是日本漢詩)來解釋概念。在《中國文學在日本》的自序中,鄭清茂老師寫道:
這本集子所收的共有四篇,可說都是我在外國遊學的課外餘業。其中三篇:「夏目漱石的漢詩」、「中國文人與日本文人」和「永井荷風與漢文學」,是在「中國文學在日本」的總題之下,先後發表於「純文學」月刊的文章。另外一篇「王次囘研究」,原載於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十四期(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因為我研究日本文學,特別是中日文學關係的副產品,所以也收進這個集子裏了。(《中國文學在日本》,第1-2頁)
以上便是《中國文學在日本》編成的基本介紹。文學創作當然不會只是受到單一元素影響,因此書中也以相當篇幅介紹了作家的個人生平,並兼述當時後的日本歷史背景與文化價值觀。鄭清茂老師自稱是夏目漱石的「愛讀者」,在〈夏目漱石的漢詩〉一文中,除了列舉夏目漱石的漢詩作品詳加分析以外,也闡述了夏目漱石的生命軌跡與人生觀。
書中還說明了許多日本古典文學相關知識,比如「萬葉假名」的幾種用法,以及鄭清茂老師對日本文學的三大批評詞彙之一,古代文學的基本精神「物之哀」定義的個人歸納:
「物」只一切客觀對象;「哀」指所有主觀情意。託物陳哀,移哀就物,而進入一種主客相融的精神狀態。具體一點說,人生而有七情六慾,情有所動,慾有所發,都逃不出道德習慣的規制。結果,是非善惡因之而分;勸懲褒貶因之而起。譬如光源氏屢次追求不義之戀,從儒、佛觀點就難免惡行之譏。但假如站在客觀的立場,認為那是「人情」上無可奈何的事,而把「光源氏的所作所為,視同出於淤泥的蓮花,只欣賞其美色幽香,忘掉污水臭泥。」(「小櫛」大旨)那麼他的不義惡行不但不必深責,反而是值得讚美了。本居宣長的這個譬喻很明顯的出自周敦頤的「愛蓮說」。總之,人情有善惡,物理無是非,所以如能移人情於物理之中,把人的存在視同物的存在,便可超越是非善惡的道德羈絆,達到只見人情之美,而不見人情之醜的境界。這種境界大概就是「物之哀」的境界了。在這個境界裏,人也變成了一種客觀對象的藝術品;而人情之慾等於培養這種藝術品的肥料。(《中國文學在日本》,第147-148頁)
《中國文學在日本》的視野並不侷限於東亞文化圈在文學創作上的相互感染,西方文學對日本文學造成的影響也不會少見於書中。儘管發表年代距今已有半個世紀,《中國文學在日本》至今讀來也仍是一本內容豐富深入,但又不失輕鬆好看的知識性讀物。來到東華大學圖書館的鄭清茂藏書庫時,不妨拿這本小書中提及的文學作品與書架上的鄭老師藏書細細比對,相信您將會更清楚地瞭解這些藏書在清茂老師的研究脈絡中與心目中的意義,以及它們存在於日本文學史上的意涵。
相關作品
- 最後更新:2025/03/27
- 瀏覽次數: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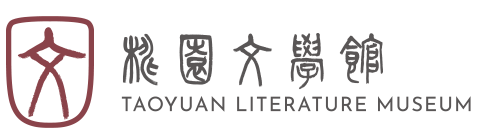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桃園文學館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桃園文學館